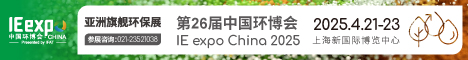并非仅仅说不:垃圾焚化的台湾经验
10多年前,台湾当局也曾启动“一县市一焚化炉”的庞大计划,导致民间的反焚化炉抗争在全岛集中爆发。1999年到2003年,经居民与环保团体持续抗议和游说,最后让三分之一数量的焚化炉取消建造或无法运转。但反对并不是全部。民间社会同时进行倡导、实验、推动垃圾源头减量,帮助政府找到了正确的、永续发展的政策方向。
海峡对岸的对抗焚化炉经验是:减量、分类、资源化才是垃圾政策之本;对垃圾焚化厂,比反对更重要的,是社会的监督和利益共享。
台湾曾将“一县市一焚化炉”作为解决垃圾问题的政策。
1999年,民间团体公布“台北市的焚化炉致癌负担是美国加州标准的两千多倍”的研究成果,这被认为是政府没有做好前置的垃圾分类、减量和回收的恶果。
2005年,民间压力下,台湾营建焚化炉的“兴建工程处”解散,“一县市一焚化炉”政策成功扭转,反焚化炉运动进入平静期。
当中国大陆各地的垃圾焚化厂引起居民抗议的时候,海峡对岸的垃圾焚化厂面对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垃圾不够烧。今年11月初,台北县由于资源回收见效,垃圾车常装不到一半,甚至垃圾焚化厂贮坑存量还出现低于警戒线的情形,县环保局开始规划明年起从一周6天收运垃圾减为5天。台北县不是孤例。此前台北市已经是每周收5天垃圾,台南市每周收4天。台北的3个垃圾焚烧厂,总装机日处理量为 4200吨,但全市每日的生活垃圾,已经从10年前的3695吨减少到只有1500吨。
台北市环保局简任技正(官衔名,相当于高级工程师)卢世昌告诉本报记者,“10 年前觉得会不够用,准备总共盖5座,现在反而3座还多了,有的厂可能要慢慢做转型,成为博物馆、环境教育中心。回头想想当初的焚化炉发展政策,应该是在建造焚化炉之前先做垃圾减量;如果不减量,以我们的环境承受能力,能盖多少座?”
而卢世昌表示,政府放弃大量兴建垃圾焚化厂的计划而将垃圾政策转向,始于民众抗争。
从零散抗争升级
“不再是‘别在我家附近盖’就好,而是政府的政策错了!”
说起反焚化炉运动,台湾环保组织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简称“绿盟”)协会监事陈建志首先想起的是,1999年,在台中县计划建设焚化炉的大安乡南埔村,美国反焚化炉专家PaulConnett在村里庙门口地坪,用大多数人听不懂的英语,通过环保团体人士的翻译,跟当地乡亲父老演讲的情形,“真是一幅有趣的画面”。
1980年代台湾社会飞速发展,在增设掩埋场的同时,1991年建造了第一个垃圾焚化厂。1 9 8 6年,“行政院”科技会议决定垃圾“以焚化为主,掩埋为辅”的处理方针,并把焚化处理列为中长程垃圾处理方法。
这期间也正是台湾走向民主化的阶段,“作为‘邻避’(英文N ot InM yBackY ard,‘别在我家后院’,简称N IM BY)设施,掩埋场和焚烧厂都有民众抗议。”卢世昌说。
台湾环保署于1990年计划兴建大型垃圾焚化厂21座;为了解决台湾各县市垃圾处理设施不均衡的问题,台湾环保署甚至在1991年将“一县市一焚化炉”作为解决垃圾问题的政策。1998年开始,台湾垃圾进入高峰期,家户垃圾日产 24800吨,政府的说辞是“垃圾危机”,建造势在必行。
政府建造焚化炉,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垃圾分类,只是将垃圾非强制地分为可燃和不可燃。但焚化炉产生的各种有毒废物中,最令人们恐怖的是“世纪之毒”二恶英和重金属,若不进行垃圾分类,焚化后的毒物排放将难以控制。
当年的环保团体,多是从关心受害地区的角度,支持选址附近的民众抗争。但是往往事倍功半。他们从零散的“攻防战”中领悟到,不能仅仅是在“邻避”的消极层次上,而是“应该在政策的高度进行关注”。
1999年7月,陈建志所在的环保联盟台北分会(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前身)与看守台湾研究中心(简称“看守台湾”)合作,邀请美国反焚化炉专家、纽约圣劳伦斯大学化学系教授柯保罗博士(PaulConnett),在台湾西部的八九个县市巡回演讲,这些演讲直接面对焚化厂选址附近居民,逐渐地,几乎每个县市都有反焚化炉团体与社区组织出现。
陈建志回忆说,国外专家带来了新的视野和高度。“台湾的相关环保单位,说服公众的时候,总是说欧美日发达国家都用这个先进方式来处理;那么乡民们现在听听这个美国专家,来讲为什么要反对焚化炉。不再是‘别在我家附近盖’就好,而是政府的政策错了!譬如,焚化的方式更花钱,并且产生新的毒物,将垃圾问题复杂化、扩大化……有了这些国际的奥援,我们也了解了思考垃圾政策的走向———减量、分类、永续社会的替代方案,作为论述的佐证。”
从这一年开始,反焚化炉行动从零散的“邻避”抗争,升级为全台湾串联。而绿盟于 2000年独立成新社团后,将“垃圾减量就能解决垃圾问题”作为观念主轴。“垃圾本来就是资源,只是放错了地方;以之前专家做了20年的台湾垃圾成分分析结果来看,纸类、塑胶类和厨余占了垃圾七八成,若能回收,剩下的垃圾只有两三成,跟全部拿去烧,出来剩下的废渣两三成是差不多的,危机根本就不存在,还能节约成本、减少污染。政府轻忽鼓励资源回收和垃圾分类,经费全部放到焚化炉,是错误的。”
1999年年底还发生了一件事,民间团体环境品质文教基金会公布“台北市的焚化炉致癌负担是美国加州标准的两千多倍”的研究成果。陈建志认为,这正是政府没有弄清楚政策优先次序,没有做好前置的分类、减量和回收的恶果。“引进先进技术的时候,并没有引进相应的运作良好的社会配套条件,因此宣称的先进科技‘神奇功效’并没有发挥。”至于“良好的社会配套条件”,环保团体认为,除了以分类减量为先导,还要落实当地民众对焚烧炉进场运营的管制监督。
官民博弈
行政机关低姿态沟通,环保团体力行监督查违法垃圾
作为最早营建焚化炉、也被监督得最严密的“首善之城”,台北市要做很多与居民沟通的工作。于是,一个沟通机制产生了:“市民参与,专家代理”。
“焚化炉是很专业的事情,但一般民众未必了解,他们有些会接收到很多错误信息,想当然,这样就很难沟通。”卢世昌提到,当年他们的内湖焚化厂作为示范厂开放给台湾各县市的县民来参观,有个老太太看到有树有草,就去拔:“她说,不是会寸草不生吗?会不会是假的?我就说,您拔拔看吧。”
“我们愿意让居民参与;但我们建议让他们信得过的专家代理,与市政单位来讨论。”也就是,让市民指定专家做调查,环保局付专家的费用,“这样对话比较有效率。”
“我们这边的状况是这样:市政府行政,民意机关要通过。”卢世昌说,“环评通过之后,要跟市议会报告,一般还是会通过预算;但是居民的要求也会照顾到,因为议员要让市民知道有为他们说话。”
各地的掩埋场和焚化炉都会有回馈制度,通常以地方性立法“自治条例”规定。以台北市为例,掩埋场一年付出1500万新台币反馈给当地,其中最基层的里(行政层级,相当于大陆的街道),要保障70%的资金(因为受影响集中于所在里)并进行自来水补助、电费补助、免垃圾费。而焚化厂,则每烧一吨垃圾给所在区200元回馈金,也就是每日超过30万元,保障20%给所在里,而相应区域则成立管理委员会管理回馈金。
为了让社会消除疑虑,与居民“拉近距离”,行政机关想尽办法。新竹市环保局将全局的办公室设在垃圾焚化厂。而台北1998年完成的北投厂,模仿在维也纳参观的“古典城堡式”焚化厂,将外部请艺术家美化,还在烟囱上设置了一个相当于 44层高的旋转餐厅。在台北101大楼建设之前,这算是台北市的地标。而其他县市的后续建成的几个焚化厂,甚至请贝聿铭设计。
以北投焚化厂为例,这里建设有巨大的文体中心,内设有SPA区水疗按摩池、温水游泳池、各类球场等等,周边邻里地区内湖区、南港区、文山区、北投区及士林区的区民可凭身份证明免费入场。类似的“回馈设施”,已经是建设焚化厂的惯例。在每一个焚化厂和掩埋厂,都有温水游泳池,免费让附近居民使用。
但附近的居民并不领情。自台北北投焚化炉开始营运,其附近居民就开始遭受焚化炉臭味的困扰。他们观察到当运送一般事业废弃物的垃圾车进入焚化炉时,臭味会更浓。卢世昌说,这中间有很大的经济动因:医疗废弃物处理一吨要5万元,如果偷运进入焚化炉,处理成本只需两千元,却可能给周边环境带来恶劣影响。受不了焚化炉的恶臭污染,居民们就自发性地联合社区中的教授、老师、退休的公务员和企业人士,甚至还有检察官,组织了一个称为“唭哩岸环保志工团”的环保团体,长期对北投焚化厂进行监督。
召集人王培英表示,志工团工作内容是,不让“不肖的”垃圾代清业者,将违法的垃圾送进焚化炉;同时积极做社会环保教育,倡导居民做好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以及垃圾减量的工作;监督焚化厂及相关政府单位,做好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并督促政府对居民的健康做病理医学研究。
王培英表示,他经常半夜带着团员和检察官去突击北投焚化炉,被查获的非法垃圾,包括废轮胎、废电缆、土壤,甚至有医疗废弃物,因此,“那些违法业者,现在‘跑路’的‘跑路’,被抓的被抓。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很踏实地监督焚化炉,这样我们所吸的空气才会新鲜一点。”
现在台北的焚化厂,不用任何事先通知,就可进入焚化厂。民间监督、抗衡的结果是,如今在台北的焚化炉所在地,都会成立民间的监督委员会,委员有当地民意领袖,还有学者专家;焚化厂每两个月,要把运行状态的各个指标公开上网,废水、废气和废弃物的排放要一目了然,市民可以质询。在台湾环保署网站上,对公众公开的,还有焚化炉与民营业者之间的经营合约。为了方便市民检查,台北市环保局在垃圾倾泻平台上设置了录像设备,并连接网络,市民随时可以上网去看进炉烧的是什么。
民间发力
台湾各县市相继停止10个焚化厂的建造计划,另有两座建成的焚化炉不运作
在2002年9月,一些反焚化炉团体及社区组织在台东成立了“台湾反焚化炉联盟”,联盟成立后的接下来几个月,刚好是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预算案的会期。
反焚化炉议题得到一些“立法院永续会”成员“立委”的关心,当时立场比较倾向环保团体的,有赵永清、赖幸媛(现任“陆委会主委”),他们长久以来与环保团体互动密切,愿意尽力去改变既定政策,而在他们承诺支持下,民间团体在2002 年10月共同发起“拒绝让焚化炉继续燃烧毒害我们的未来”联署,并获得122个民间团体的支持,要求立法院删除环保署2003年度焚化炉相关预算近37亿新台币。
之后一个月,在几场回应环保署答辩的记者会中,民间团体指出焚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是建设计划已经超出台湾垃圾处理的需要,似乎只为花完预算,而不顾实际需要。其次,一般性的工业废弃物被允许进入焚化厂焚烧,企业占用所有纳税人支持的设施完成自己的生产流程,对纳税人不公。第三,已经投产的焚化厂有严重的污染排放问题。第四是政府经费预算过多花在末端处理,却在源头处理(分类、减量、资源化)上预算额极低。此外还有焚化炉剧毒灰渣的处理问题。
虽然时任“环保署长”的郝龙斌(现任台北市长)受到了“立法委员”的严厉批评,但环保署的预算还是过关,而焚化炉兴建计划也持续进行。不过,环保团体与“立法委员”们并未放弃。“立法院”永续会先是举行公听会,让环保团体与社区组织直接批评环保署长;继而有“立法委员”建议举行“废弃物政策高峰会”,让高层官员听到人民的声音。
2003年废弃物政策高峰会前几天,环保署宣布两座焚化炉停建。但在高峰会上,民间团体还是提出四点主要诉求:立刻停止未完工之焚化炉的兴建;将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推动资源回收及厨余处理;对于焚化炉的操作资讯,包括进场垃圾来源、种类、操作过程、排气检验结果及飞灰底渣的处理,都必须公开给社会监督;加强焚化炉管理的地方及社区参与监督机制,因二恶英排放事关重大,对操作厂商的要求及管理,必须大幅加强。
废弃物政策高峰会后,到6月,又有两个社区———台北县新店安康和中台湾小镇集集———加入了这场运动。媒体聚焦之下,当时的“环保署长”郝龙斌辞职了,他认为“民意不应凌驾专业”。
陈建志感觉到,行政单位内部,观点不尽相同。而台湾地方自治的制度,也让环保组织有了“空子”可钻。“县市首长也是我们游说的对象。他们出于选票考虑,担心民怨过大影响自己的选举。”此后,台湾各县市相继停止10个焚化厂的建造计划,另有两座兴建完成,但地方政府不同意而无法运作。2005年,民间压力下,环保署把营建焚化炉的“兴建工程处”解散了。成功扭转“一县市一焚化炉”政策后,反焚化炉运动进入平静期。
分类、减量
“不是什么都可以烧”,逐渐从公民的诉求,转为政府的公告
与反焚化炉运动同时进行的,是民间团体推动的垃圾源头减量。
“当然是民间推了资源回收之后才去做分类。民间先喊,政府推动。”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董事陈曼丽说。主妇联盟成立于1987年,这个制造台湾第一只环保袋的社团,由一群热心的“妈妈”所组成,是台湾少数以女性为主导的环保团体,以“大地之母”的概念介入环保。跟以抗争、论述见长的环保组织相比,她们的风格是“行动与生活结合”。
从1988年以义工身份加入主妇联盟,主妇联盟董事陈曼丽已经与这个团体相伴超过20年,其中十几年相继担任过秘书长和董事长,从成立之初,到学校、社区倡导垃圾分类,到反焚化炉运动烽烟四起的时代敦促政府回收厨余,陈曼丽见证始终。
厨余垃圾占垃圾的35%左右,水分和盐分含量大,环保界认为,在掩埋场,是产生恶臭和污水的主要原因;在焚化厂,会造成炉温下降,燃烧不完全,以及盐分中的氯,会产生较多二恶英以及有害气体。陈建志表示,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主妇联盟比较专注做资源回收和厨余回收,效果不错。”从1998年开始进行一系列实验之后,2000年,台北市政府开始在两个里进行5000户家庭的试办计划,由主妇联盟负责执行,由台北市清洁队负责清运,回收成果斐然。台北市其他里民也要求加入,于是,台北市扩大厨余回收区域,增加到51里,并在2003 年底宣布449个里全面回收。
逐渐,垃圾政策也成为台湾各县市竞争的舞台。最早实现厨余垃圾全面回收的是台中市,地方首长为了表示自己“呼应民间诉求”,体现“进步性”,相继效仿;而从2002年开始,台湾环保署也编列预算推动厨余回收;到了2005年,环保署制定垃圾强制分厨余、资源(可回收)和一般垃圾三类的政策,不分类则拒收、处罚。厨余回收再利用政策推行以来,厨余回收量由平均每日80吨,提高到每日 2000吨以上,相当于两座垃圾焚化厂日处理量。
台北市的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需焚烧的垃圾需以政府特制垃圾袋装,按容量计费;可回收利用垃圾不计费,由经济诱因推动垃圾减量),也是“绿盟”影响市议员的一大成果。最初,政府对分类政策并无信心,认为民间水准不够;但经过环保团体试行之后效果不错,“通过我们游说,议员了解我们的诉求,于是提议案,推动成功。”陈建志说。
2000年7月,台北市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三个月之后,垃圾量锐减,10月就改为一周只收6天垃圾;到2003年5月,垃圾量持续减少,收垃圾时间变为5天。政策导致官民双赢:当时的市长马英九曾经穿着围裙上电视宣传的政策,成为他市长任上最突出的政绩,导致他连任成功。
垃圾费随袋征收,政府的垃圾收集车只会收由市环保局指定的专用垃圾袋。垃圾袋售价为每公升新台币四毛五(相当于人民币不到一角),最小五公升,最大120公升,市民可以在指定的地方如便利店购买。路边的垃圾筒是给行人用的,如果被发现扔家庭垃圾,会被处以最低1200元新台币罚款;如果扔的垃圾没有使用专用垃圾袋,罚款则从2400元起跳。使用伪造垃圾袋将被罚款新台币3万至10万元,举报的市民可以获得两成罚款作为奖金。
每日下午4点半开始,台北市内180条跟公交车路线类似的垃圾回收线开始运作。每条线路上分20个停车收集点,市民必须等待垃圾车队来,才能从家里拿出垃圾直接放到垃圾车及资源回收车上———这就是“垃圾不落地”。车队分资源回收车、厨余回收车、一般垃圾等,市民必须对家里的垃圾进行粗分类,如灯管、保丽龙材料容器、塑胶袋、废纸、干电池等,不允许放入一般垃圾;只有一般垃圾需要放入收费的垃圾袋,这意味着厨余和资源垃圾都不需要付费处理。资源垃圾将卖给资源回收分类场;厨余按性质分为两类:生厨余用来堆肥,而煮熟、含盐分的食品则为熟厨余,经过消毒过滤粉碎,用来喂猪。
下午走在垃圾收集线路上的,还有台湾最大慈善组织佛教慈济功德会的车队,一些价值较高的垃圾市民可能乐于交给慈济,因为那算是一种捐赠。而资源回收业者则通常要抢在政府车队之前,回收物资。资源回收成为社会共同参与,陈曼丽说,“很多30岁左右的年轻人,乐于将资源回收当作自己的职业,已经不再是‘酒干倘卖无’时代的底层职业了。”
以慈济功德会为例,在“洁净大地”、“惜福”等观念下做环保,已经实行近20年。慈济在台湾有4500多个环保点,动员了62000多位志工,进行垃圾的回收分类。
在众多社团紧密编织的教育和行动网络中,公民意识在短短十几年转变。“如果你的垃圾袋里有一只宝特瓶(俗称PET,常被用于碳酸饮料之包装)大家都会想: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啊?环保观念,变成了一种社会制约力量。像我家,虽然回收资源占阳台的面积,但家人都觉得那是必要的。”卢世昌说。
“不是什么都可以放进去烧”,逐渐从公民的诉求,转为政府的公告。有害废弃物、医疗废弃物,以及水银温度计、轮胎、塑料容器、餐盒、小家电、亚克力、塑胶软管、马桶盖、日光灯管、干电池、光碟片、手机、工业保丽龙、可回收衣服、报纸、杂志、纸箱、干净塑料袋、瓦斯桶、家电、汽车、厨余等等30多项,在台湾都是明文规定必须回收利用和无害化、不可焚烧的。这些不可烧的可再生垃圾,都有相应的厂商处理。慈济以回收宝特瓶制成的毛毯,已经在全球20个国家的灾区送出将近25万条。
政府逐渐吸纳了民间社会的诉求和理念,订定“零废弃政策”,这项政策将过去着重废弃物末端处理的方式,转变成源头减量与回收再利用的管理方式。“目前在源头减量上基本上做到了预算公平,堆肥和资源回收,会有奖励和补助;不建焚烧炉的地方,要转运到外地焚烧,会有补助。”陈建志说。回收垃圾的处理厂商,可以从环保署成立的资源回收基金管理委员会得到资助,这每年50亿补助的来源,是相应商品的生产厂家。
零废弃目标
不是更多的焚化炉,而是更少的垃圾,乃至零垃圾
2010年上海世博会,台北以“资源全回收、垃圾零掩埋,迈向城市的永续”作为两项参展主题之一,布展还将以大型垃圾车为主造型。目前台北市每天产生1200吨回收物和1500吨垃圾,也就是资源回收达到45%.废弃物部门温室气体排放也由1998年222万吨下降至2006年64.42万吨,减量达71%.“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国际许多都市都已经将台北在资源回收工作方面的成就当做学习对象,不过我们未来将持续努力,希望在2010年达成‘资源全回收,垃圾零掩埋’愿景。”去年7月,台北市长郝龙斌告诉本报记者。
这个愿景基本可以达成。台北市焚化炉一天产生的38吨飞灰本要加化学药剂制成 52吨的飞灰稳定化物掩埋,而炉底渣则再利用,作为道路管沟回填。不久前启用的新技术,则是将飞灰中的盐分水洗及将重金属稳定化之后,以1比300的比例作为原料制成一般水泥,达到“全回收”。
但民间社会尚未满足。当初与绿盟并肩作战的“看守台湾”,进一步在呼吁禁用、限用产生二恶英的材料PV C,而绿盟则在关注河川污染和温室气体。陈建志表示,各个县市的焚化炉监督,是良莠不齐的。“下一阶段,在各县市,台北的做法应该一体适用:社区居民经过训练,可以随时进入厂区做督促和检查,全面形成监督的力量。”陈曼丽说,回馈金的使用也要民主化、透明化;另外,环保署应要求管辖下的焚化厂订出温室气体减量的目标。
不过,至少在一点上,民间与政府达成了共识:不是更多的焚化炉,而是更少的垃圾,乃至零垃圾。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添加“谷腾环保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