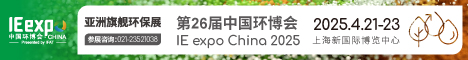南都周刊:我的垃圾我的城
垃圾围城
垃圾是城市的附属物,城市和人的运转,每年产生上亿吨的垃圾。
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城市,正在遭遇“垃圾围城”之痛。
2005年《各地区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情况》显示,当年全国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仅为51.7%。建设部2006年调查表明,全国600多座城市,有1/3以上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
2009年3月,北京市政管委会主任陈永疾呼,北京垃圾危机即将出现,“这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在北京,“垃圾围城”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83年,垃圾简单的填埋方式,导致北京三环路与四环路的环带区上垃圾成堆,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座!为突破重围,北京市斥资23亿,才逐渐攻陷这座惊人的围城。
20多年后,垃圾巨兽卷土重来,日产垃圾18400吨,垃圾处理缺口8000吨,67%的高缺口率,如一颗巨型“炸弹”,隐藏在城市地下。
一边是不断增长的城市垃圾,一边是无法忍受的垃圾恶臭,成为城市垃圾处理中的棘手问题。
在北京最大的垃圾处理场——高安屯,无论是填埋带来的恶臭,还是随焚烧滋生的二恶英,正威胁着附近居民的生活。不想戴着防毒面具,有人无奈选择了离开,有人积极站出来进行环保战,上街散步,制作宣传画,他们的生活因垃圾而改变。
在广州,开展了10年的广州垃圾分类工作面临诸多严峻的现实问题。2009年4月,是否取消垃圾分类成为广州热门话题。而这个热议背后,是日产垃圾9776吨的广州,2010年将面临的垃圾围城危险。
高安屯环保反击战
鉴于填埋、堆肥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事实,焚烧一度被认为是更环保的垃圾处理方式。正在这场垃圾焚烧“潮流”愈演愈烈之时,各种纷争也此起彼伏。
3月27日早晨,俞东来到单位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写“臭气日志”。“那股味又萦绕在周围了,起床时似乎觉得不对劲,这一出门便是明证啊。”
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六篇了。前几天的日志里记述的状况更让他心烦:“夜10点21分,去物业所在楼交水费(自动刷卡机),出门便闻到一股难闻的垃圾焚烧味道,不敢大口呼吸,这种味道让人特别难受。”
他不知道这篇《高安屯臭气日志》何时才能“杀青”。从去年9月30日开始,也就是北京朝阳区市政管委会对公众道歉、并承诺治理高安屯垃圾场恶臭的20多天后,“臭味日志”正式诞生。这个日志注定没有太多读者,但它的背后是20多万同样饱受恶臭之苦的小区居民。
32岁的俞东话语温和,他不曾像其他居民一样戴上口罩去街头散步,但他说,写日记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2008年6月,这位平面设计专业的教师,住进了朝阳区的优点社区,南北通透的户型,每平方米7000多元的价格吸引了他。“搬来之前就知道垃圾场的事情,也向不少人咨询过,但小区里的人说不是特别严重。但过来之后,发现味道越来越重。”后来,他用GOOGLE EARTH测量了下,自己家距离高安屯垃圾场仅有3公里。
他的妻子是幼儿园老师,两人都到了生育年龄,家里人也急着抱孙子。但不时传来小区里有孕妇流产和兔唇婴儿出生的消息,让他们有些犹豫。“如果非要生,可能会租个别地的房子吧。”
给俞东夫妇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高安屯垃圾场,全名是朝阳区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当地居民介绍说,1980年代中期,此地还只是附近居民倾倒垃圾的大土坑,到了1995年,被改造为垃圾处理场,2002年,成为朝阳区的垃圾卫生填埋场。2008年 7月,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厂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北京垃圾场多达16座,为何高安屯的恶臭令人如此难以忍受?
萝卜快了不洗泥
原先住在高安屯的居民已经被搬迁,现在马各庄,则成了是距离高安屯垃圾场最近的居民区,仅有600米。一位陈姓村民说,早年的垃圾场并没有臭味,他们也没在意。“从2005年开始,路上的垃圾车越来越多,臭味就严重了。”
600亩大的垃圾场方圆几公里内,分布着万象新天、天赐良园、榆景苑小区、柏林爱乐、优点社区等居民小区,以及北京物资学院等数个高等院校,常住居民已达数十万人。此外,正在兴建的北京市规模最大的两限房“常营两限房”,距离垃圾场仅1500米。
2002年入住柏林爱乐小区的赵蕾,感受比俞东夫妇更深刻。在她记忆里,2005年偶尔有味道,2006年每个月闻到一两次,2007年每个星期能闻到,2008年基本就是天天每时每刻都能闻到。赵患有呼吸系统疾病,臭味让她喘不过气来,她经常夜里两三点被憋醒。“特别是去年奥运期间,夜里不敢开窗户,醒来就戴着防毒面具,打开电视,躺在那里耗时间。”赵蕾说。
2009年4月7日,记者驱车从后门进入戒备森严的高安屯垃圾场。让记者略感意外的是,场内绿化工作并不差,树枝吐绿,春草返青,黄蓝色小花点缀其间随风摇曳。到了作业区附近,方才恶臭扑鼻。朝垃圾场西南方望去,“常营两限房”正拔地而起,工地上一片繁忙景象。
在北京16座垃圾填埋场中,高安屯的设备最先进,也最具争议。
王维平是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工程师,是北京市垃圾处理的智囊人物。“有臭味的垃圾场大多没有按规定运行。”他说,“按规定运行是有国家标准的,比如说垃圾来了当时就得推平压实,暴露的垃圾作业面积不能超过660平方米,排出来的水当天就得抽走。如果放那一个月,能不臭吗?都成黑汤子了。”
与高安屯形成对比的是,北京北神树垃圾场运行非常规范,房地产开发商都很喜欢靠近它,称它为生态公园。“不仅没臭味,还漂亮得跟景山似的。”王说。
“凡是我们市属直管的垃圾填埋场,都没臭味,没有超标,没有老百姓示威游行。但区属的,比如高安屯、六里屯的垃圾场,对方不听我们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官员的升迁撤职,由区委区政府决定,不是市政管委会决定。”王维平把原因归结在垃圾场市属与区属的差别上。
这些垃圾场的管理者也是有苦难言,他们有“客观情况”。王维平说:“萝卜快了不洗泥。高安屯填埋场设计能力是1200吨,现在每天进4700吨,它能没臭味吗?”
3月9日,北京市政管委会主任陈永公开表示,北京垃圾危机即将出现,“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目前北京的16座垃圾填埋场,设计总处理能力为每天1.03万吨,而现在北京的垃圾日产量为1.84万吨,处理能力缺口每天高达8000余吨。
一边是不断增长的城市垃圾,一边是业主抱怨的垃圾恶臭,垃圾处理部门左右为难。从环保角度考虑,高安屯垃圾场整体搬迁无疑能大快民心,但搬到哪里去是个问题。
“搬得越远越好,搬到无人的荒郊野外,这当然是一种想法,可惜也不切实际。如果垃圾场选址太远,垃圾运输的成本将大大提高。王维平解释:“垃圾车的合理运输半径是多少?14.5公里,超过这个运距,吨成本就不合理了。天天都要运,财政将不堪重负。”
这意味着,多数居民最盼望的垃圾场搬迁方案,实现的希望极为渺茫。
垃圾围城下的抉择
跟踪了20年的城市垃圾,王维平被视为国内垃圾研究的第一权威。跟很多刻板的专家不同,他不仅懂垃圾也能拉一手极好的二胡,在他眼里一曲《二泉映月》也饱含着“垃圾的忧伤”。
1983年,北京曾遭遇过一次严重的“垃圾围城”。王维平回忆说,当时利用遥感技术发现,沿着北京三环路与四环路的环带区,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堆!“垃圾包围城市”名副其实。为突破重围,北京市斥资23亿,赶工建设了23座垃圾处理设施,才逐渐攻陷这座惊人的围城。
此次垃圾巨兽卷土重来,来势更加凶猛,袭遍全国。《人民日报》4月1日援引建设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600多座城市,有三分之一以上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
“一旦垃圾桶变成了一个炸弹,谁都会把它放在第一位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环保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赵章元说。他遗憾地表示:“垃圾桶都在角落里,各级政府以往同样把垃圾问题放在角落里,没人重视,以至于今天矛盾激化。”
如何拆除这枚巨型“炸弹”的引信?20多年前,北京的选择是填埋;这次,答案变成了焚烧。
2008年7月28日,也即北京奥运会倒计时的10天之际,北京市首座大型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厂建成并投入试运行。当地媒体报道如此描述它的重大意义:“这意味着北京市的垃圾处理方式由填埋开始转向焚烧处理。”当然,对附近的居民来说,填埋场的旧臭未消,垃圾焚烧又添新忧。
北京市政管委会的资料显示,目前北京市处理的生活垃圾中,94.1%采用卫生填埋方式,3.9%采用堆肥方式,仅有2%采用焚烧方式。与国内其他城市比较,北京已经远远走在深圳之后:深圳已建垃圾焚烧发电厂7座,日处理垃圾11370 吨,焚烧发电处理量已占总处理量的40%以上。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聂永丰,被认为是学术界坚定的“焚烧派”。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的困难,根本原因在于处理能力严重不足,且处理方式单一。
在北京市相关管理层中,焚烧已经成为主流意见,市政管委会各类公告中,“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速度”成为曝光率极高的一个短语。而这个理念,最早正是由王维平提出来的,“北京填埋不是方向,就得发展焚烧,综合治理也在积极探索。”
放眼全国,大规模的垃圾焚烧建设高潮已经掀起。王维平掰着指头,历数已经拥有焚烧炉的城市:哈尔滨、大连、天津、北京、上海、深圳、宁波、温州、武汉、重庆、广州、太原??这个名单中的城市还在不断增加中。
北京正在加快焚烧的步伐。3月,北京市政管委会主任陈永表示,要在2015年实现40座设施的建设,其中,将加快5座垃圾焚烧厂的建设。目前,高安屯厂正在调试中,南宫的土地已获批复,六里屯焚烧厂正在进行专家论证,目标是保证2015年焚烧量达到8000吨,这正是目前北京垃圾处理能力的一个缺口量。
与此同时,与垃圾焚烧有关的争议也日趋白热化。争议的焦点,就是焚烧产生的致癌物质二恶英。
焚烧背后有利益集团?
60多岁的赵章元,是目前国内坚定的“反焚烧派”,他认为焚烧不是一种最好的、科学的垃圾处理方法。“污染不可避免,其中二恶英是谁都不敢否认的一级致癌物,不管你排放控制多好,它总会有,就按照欧盟标准0.1纳克(1纳克就是10的负九次方克),但它的累积效应是最可怕的。”
他介绍说,二恶英的半衰期是14—273年,等衰减完了需要百年左右,基本就可视为不降解。它在人体里累积之后,会越来越多,迟早还是要发病的,无法避免的。不管在欧洲还是日本,焚烧炉周围民众都出现了癌症高发区。
力主“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速度”的王维平,也承认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有致癌作用。但他表示,可以遏制它产生的量,处于对人体健康的范围内。理论上,垃圾焚烧温度在320度与820度这个区间之外,不会产生二恶英,所以需要在3秒内从820度以上快速降到320度以下,“这样二恶英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你没有更好的技术取代它,除非你不产生垃圾。”王维平的话中透着无奈。
让赵章元担心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目前国内不严格的管理状态。“现在国内约50台焚烧炉,几乎都是处于不饱和等不良状态下生产。如果焚烧处于不正常状态,那二恶英的浓度就会更大了。”这个“不正常”,包括工作程序上的简化、过分降低成本等多方面。
垃圾焚烧,二恶英,这都是略显专业的名词。但等到业主们逐渐了解后却更加不安,这种看不见闻不到的致癌物质,比臭味更让人恐怖。
很多人选择了逃离。“上周我又送走了3户,如果这儿不改善的话,我也会搬。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命都不要了。”赵蕾说。
俞东也有过卖房的想法。2007年6月他买房的时候价格还比较低,每平米7200元,总价80多万。现在小区的房价受到垃圾场影响,略微下浮,但仍在9000元左右。“现在卖虽然不怎么赚,但也不会赔。问题是,卖了后怎么办,这点钱在别地根本买不到这么大的房子。”
搬到哪里去也是一个问题。“到处都要建焚烧场,你能逃到哪里去?”
在很多中国的市政管理者看来,垃圾焚烧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处理技术。但赵章元的看法恰恰相反:焚烧已经处在被淘汰的路上。
“不管日本还是欧美国家都在想办法关停,日本停了2/3,欧洲很多国家都提出禁烧令,并提出在2010年实现不向环境中排放这类污染物的口号。‘禁烧风’才是世界主流。”他认为,有些政府官员思维是滞后的,有些政府部门的做法也简单粗暴:政府计划好了焚烧,你就不能反对。
作为国家环保总局评估中心组的专家,赵章元评审了很多省份的焚烧设施。大量的实际勘察与资料分析后,他逐渐坚定了反对焚烧的立场。让他最头疼的是,焚烧派已经形成了一种利益集团。“发达国家的焚烧炉商,是利益集团的第一部分人。他们千方百计来中国推销他的产品,因为在他们国家已经进行不下去了。第二部分人是国内的项目承担者,他们或者承担某地区垃圾焚烧任务,或者是研究垃圾焚烧的大学教授,都得到充足的项目经费。第三部分人则是某些政府管理人员,他们给垃圾找出路,心情迫切。”
他已经感到了这个利益集团的强大,一个让他吃惊的例子就是“300米标准”的突然出台。
在环保部发布的环发〔2008〕82号文件附件中的“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的技术要点”中规定,焚烧炉和居民区的直线距离不得低于300米。“这个300米怎么出笼的?可以肯定,是在少数人不正常操作下搞的。”赵章元说。
北京市围绕六里屯这个垃圾焚烧厂的问题争论了很久,距离问题在专家论证会上争论得很激烈。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做了个计算模型,污染物扩散到一定距离,浓度达到欧盟标准,算出来还不到300米,说已经考虑风险了。“但是我认为这个结论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专家组长决定不能这么写,当时300米就划掉了。”
然而,事隔一年后,环保部把那个标准突然发布了,就是300米。
300米的距离简直形同虚设。赵章元担心的是,这个标准一旦执行,全国将出现可怕的局面,甚至一场灾难可能要降临。“为什么说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因为很危险。各省都在憋着劲建焚烧炉,好落实十一五规划,光北京市就公布了要建设20台,在京城东南西北的20台炉子一冒烟,整个首都上空的有毒气体就会一天天积累起来,大气是连通的。”
他越想越危险。
累积的信任危机
争议在继续,不信任感也一点点在累积。
周一翔居住在万象新天,这是个新兴的高档小区,也是距离高安屯垃圾场最近的大型居住区。“开始并不知道臭味是哪儿来的,半夜里被熏醒,感觉有点窒息。全是那个味道,逃不了。”2004年入住,次年,他就开始为垃圾臭味维权。
“垃圾场历险记”几乎是每个维权业主的起点,周一翔也一样。“2005年感觉味道就很重了,就跟几个朋友偷偷去了高安屯垃圾场,结果被垃圾场的保安人员发现后,关起来了。我们后来打了110,才被警察接了出来。”
之后,周一翔还与同小区的刘军等人组织了一次集体签名,呼吁政府对垃圾场采取措施,万象新天、天赐良园、柏林爱乐等多个社区的240多名业主一起签名,签名信送到了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北京市政府、朝阳区环保局等多家单位。朝阳区环保局在回复中承认,小区臭味肯定与垃圾场有关系。
随后,周一翔等人就以不同的方式来呼吁,包括跟朝阳区区长陈刚通电话。但周一翔说,臭味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还越来越严重。
去年8月30日,难以忍受恶臭的数百居民手持标语、戴着口罩,走上常营和管庄附近的街头,并拦截垃圾车,抗议相关部门的推诿搪塞。由于北京奥运会刚结束一周,该行为引起国外媒体的极大关注。因参与维权行为,周一翔、刘军、赵蕾等人都被家访,赵蕾还先后被家访了三次。“警察认为我是组织者。我能组织这么多人吗?真是高看我。”她说。
随后,朝阳区市政管委会公开向居民道歉,并承诺投入9100万元,20天内解决高安屯垃圾场臭味。但两个20天过去了,周一翔等人仍能闻见臭味,俞东的“臭味日志”也无奈地在继续。
针对新建的垃圾焚烧场,他们还申请了对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场的两次国务院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4年12月9日批复北京市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厂项目调整方案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文件,责令该垃圾焚烧厂停建、缓建或者不投入使用。2008年9月10日,国务院行政复议司最终裁决:报告合法。结果一出,周一翔等申请人极为失望,这也是对他们维权行为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2008年10月26日,在恶臭和烟气中生活的业主自制宣传画,在小区内进行二恶英危害以及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遭到城管的阻挠,宣传画被撕毁。相关视频被传到网上后,再次引发哗然大波。
尽管如此,维权努力仍然在继续。2008年11月份,柏林爱乐一居民将垃圾场告上法庭。该案的立案竟然要经过高院批准,立案最终成功。2009年1月, 该案开庭,仅允许一人旁听,至今未裁决。
2009年2月,万象新天居民拿到北京市环保局的正式回复:两个垃圾焚烧场自试运行以来,从未进行过检测,而医疗垃圾焚烧已经试运行了3年之久。“没有谁检测后敢给合格证。”刘军说。
就在业主维权的同时,情况却继续朝着他们认为“更坏”的方向发展。
在距离高安屯垃圾场1.5公里处,北京最大的常营两限房正在大兴土木。按照规划,此项目明年建成后将提供12000套两限房,与配建的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一起,构成了一座容纳几万人的庞大社区。1.5公里,这比万象新天、柏林爱乐、优点社区等任何一个小区都离垃圾场近。《新京报》评论曾经批评高安屯垃圾场“规划制定有缺漏”,而在赵蕾、周一翔等人看来,“常营两限房”更是个不负责任的规划。
“之前我们不知道有垃圾场,过来也认了。”赵蕾悲哀地说:“现在填埋起来了,焚烧也起来了,那为何还要在垃圾场附近规划两限房?”
周一翔则表示:“这种规划就是严重违反科学发展观的。”他担心,两限房的居民大多是老北京人,那时,如何建立与新业主的一种信任关系,无疑是对未来当地政府的一个极大挑战。
严重的信任危机,同样存在于富有争议的海淀区六里屯垃圾场问题上。环保作家冯永锋曾写道,海淀区市政管委会的官员声称“垃圾焚烧场运行了,臭味就消除了”,然而居民们回应说:“填埋场都无法兑现规划上的诺言,你让我怎么相信焚烧厂是安全的?”
“不要总搞背对背”
“我感觉,今年将是垃圾问题大爆发的一年。”冯永锋对未来的形势感到担忧。“如果政府还不当机立断,把垃圾分类等源头的事情做好,将来是死路一条。”
他说,在垃圾前端的控制上,有关部门政府一直没能与市民形成一种合力。他个人曾经建议六里屯附近的很多居民,自己先把垃圾分类做起来,这样维权的时候更有底气。“但他们懒得做,一听说焚烧炉又要建,就急了。这样直接把问题推给政府,其实也是一种简单粗暴。”
而根据4月10日的北京媒体报道,在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的同时,北京已经选择包括市属机关、公司、商场等100单位,做零废弃管理试点;果菜市场设有机垃圾处理设施,一些菜叶就地进行堆肥和生化处理;在每个区县10%的常住人口中,实行垃圾分类。
这个理念不仅跟赵章元等很多垃圾处理专家想法接近,也跟很多环保组织的理念贴近了。“自然之友”调研部张伯驹表示,无论填埋还是焚烧,都不能真正解决垃圾问题。“真正的解决,一定要重视前端,注意减量与分类,这恰恰是城市管理者和公众都不重视的。”
理念在接近,而重建被破坏的信任感,也许更加重要。冯永锋注意到:北京的垃圾场大部分位在城乡接合部,比如高安屯和六里屯,这些地区的市民维权意识都非常强。“因为兴建了很多新兴小区,住进去的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思维活跃。”
“如果一时解决不了,老百姓也通情达理,这确实也有个渐进过程。但不能拿我们当傻子,你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你给一个结果,我们必须就接受。”周一翔说,他最希望的,是公众与政府间能有一个畅通有效的沟通渠道。
赵章元则提醒,业主有过激情绪是难以避免的,政府部门应给予理解。“你要在我们家门口建垃圾场啊,污染得那么严重!”他曾经看到六里屯的小孩子很可怜,戴着防毒面具,说“很难受”;还曾看到六里屯维权的老人无奈地说:我们老了,死就死了,我们的孩子呢?
他认为,如果坚持垃圾焚烧道路的话,这场争论会越来越尖锐。“我不提倡尖锐化,我们要坐下来谈,不要总搞背对背。”
收买佬:什么年代就捡什么
广州人喜欢将拾荒者称为“收买佬”。在广州街头,每隔10-15分钟,就有一位拾荒者对垃圾箱进行一次分拣。他们见证了城市垃圾处理方式的变化,也从垃圾里看到城市生活的变迁。
如果你想找出100户至少养有一只猫、而且没有养狗的住家,以下就是拾荒者庄清臣从他们的家庭垃圾中获得的结论:一连收集五个星期的垃圾,你会发现有30%的这种家庭,这段期间的某一刻都丢过一份报纸。
在美国,曾经有学者做过一个“垃圾考古”,在垃圾填埋场地面打一个岩心下去,得到不同年代的垃圾成分,从而分析不同年代的美国人的消费水平、消费习惯。在广州,10万的拾荒者们,只需要掏掏街头的垃圾桶,就可以说出这座城市大概的生活
拾荒近20年,基本上光顾过广州每个区垃圾桶的庄清臣,会告诉你:天河区体育场附近的垃圾桶里10%是广告传单,而荔湾区的老广们更爱扔些带着汤汤水水的生活垃圾。
根据广州市环卫局的一个统计:广州街头,平均每隔10-15分钟,就有一位拾荒者对垃圾箱进行一次分拣。居民、拾荒者、环卫工人,构成了这个城市被称为有“中国特色和广州特点”的民间垃圾分类方式,使得每天广州大约有1000-2000吨的有用垃圾被分拣出来循环再利用。
在广州,庄清臣只是庞大的拾荒者群落里的散兵游勇。43岁的拾荒者李杏,则是正规军中的一员。
2009年4月2日,广州市环卫局邀请市民代表、相关职能部门“智囊人士”就广州垃圾分类的推广献策建言。10年间,广州街头垃圾筒,从单桶到双桶再回归到如今的单桶,取消垃圾分类一说,正在广州坊间热烈讨论。而这传言,在李杏看来,早是确定的事,“哪有什么垃圾分类,我在垃圾场捡了3年垃圾,哪次垃圾车来不是一口气卸下垃圾就跑?也只有我们挑挑拣拣。”
在广州最大的拾荒者聚集地——兴丰生活垃圾填埋场,李杏和她的同行、上百名拾荒者见证着城市生活垃圾的变迁,也间接参与了城市垃圾处理方式的改变。
“垃圾村”的变迁
一群拾荒者,蜗居在广州白云区兴丰垃圾场边的小山谷中,遗世独立,自成一体。
“脑袋系在腰杆上的活,你们这些城里人知道什么?哎,慢着,你脚下踩着一个铝盒子!”李杏很不耐烦偶然来窥视拾荒生活的陌生人。她说,很忙,没空接待参观者。
拾荒者们穿着环卫工人的橘红色荧光衣,高统水靴,弯着腰,仔细在垃圾中翻刨找寻,发现目标就立刻出击,捡起来放在袋子里。即便深夜,拾荒者弓着的脊梁依然在垃圾山中若隐若现。拾荒者的生活轴心基本就是围绕垃圾转——捡货,赶(选)货,交货。
兴丰生活垃圾填埋场,位于广州市东北方向38公里处的白云区太和镇兴丰村。由于四周山林环绕,景色优美,而且随到随填的操作方式,实现垃圾“零堆积”,这座垃圾场在宣传中被亲切地称为“花园垃圾场”。该场于2002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目前已成为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场所,每天进场的生活垃圾超过6500吨。
垃圾场上总会有寄生的“垃圾村”。兴丰“垃圾村”诞生于2004年9月,但它的前身——李坑 “垃圾村”早在l992年就随李坑垃圾填埋场的开场一同出现。2004年,李坑垃圾填埋场因使用期满关场,场内的“垃圾村”被迫解散。次年9月,一名姓刘的拾荒老板取得兴丰垃圾场承包权,招募部分原李坑“垃圾村”的拾荒者,在现有基础上重建了一座“垃圾村”。
“垃圾村”由纵横两两相对的五排棚屋构成。住过李坑垃圾村的老马已经加入拾荒行列8年了,“这里干净多了,有自来水,还通了电。”整个社区共有棚屋70余间,拾荒者140余人,大都来自湖南益阳、衡阳和岳阳。
他们都是夫妇档,每对夫妇都有一间小窝棚,捡回来的油毡、纸板、塑料膜、条幅布,都是可利用的建材,再摆上一张穿了洞的沙发或者瘸腿的茶几,就算是一个家了。每对夫妇每月收入2000多元,还可以上下浮动千把块钱,视乎你是宁愿起早摸黑还是喜欢买彩打牌。
垃圾村的历史与改革开放史高度重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废旧回收几乎全部由国营供销社网点垄断。那时,广州垃圾收运队实行“定人、定车、定时、定点”和按居委分工包干清运垃圾,居民则以铃声为号,依时将垃圾倒上垃圾车,垃圾车直接拉到垃圾场。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社废旧回收系统在市场的冲击下面临崩溃。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城市生产生活垃圾激增,得不到有效处理和回收,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对环境也造成很大污染和负担。
在体制和现实需求的双重压力下,个体废旧物资回收应运而生,“国退民进”,迅速抢占了国营企业退却后留下的阵地。现在,广州大约有废品收购站500多个,全市废品站每年回收废品物质480万吨,金属、纸张、塑料品、废旧家具等比较容易分拣的垃圾,基本通过这个渠道变卖后进行循环使用系统。
大量从河南、贵州、安徽、湖南等外来农民工来广州投身拾荒,“垃圾村”不断出现。某种程度上,“垃圾村”可视为中国城市化的伴生物。
垃圾里的生活
现在垃圾场拾荒已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先由拾荒老板拿出一笔资金,从政府主管部门那里,将垃圾场承包下来,再由拾荒老板招募拾荒者,捡到的废旧物品必须全部卖给老板,老板再用高于收购价的价钱将其卖出,赚取差价,拾荒者就相当于老板雇佣的工人。老板在垃圾场内设有一个露天堆放场,每对拾荒者夫妇都有一小块堆货地,他们会视捡货的量而每天或隔几天到堆放场“赶”一次货,然后在第二天凌晨交货。
“广州人生活得真不错,看看他们扔的东西??”老马眼尖,将一个空瘪的烟盒从一堆垃圾中挑出来,里面还有3根红双喜。“我经常捡到一些好球鞋,都寄回老家给我儿子了。”忘了说,老马手机里的SIM卡也是淘的,号码很不错,带3个8。
他们的闲暇时光也与垃圾紧密相连:读垃圾中捡来的书、看垃圾中捡来的碟、听垃圾中捡来的磁带,孩子们还有一两件垃圾中捡来的玩具。
“可以说,垃圾里头藏着人类行为,也记录了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脚印。”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说,“想要了解垃圾,研究它,首先就得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对拾荒者说,垃圾的前世今生就是肩上那道重荷。老马是2001年跟着叔叔来广州拾荒的,那时才20岁出头。叔叔告诉他,小子你命好,现在的垃圾又轻又贵。“1990年代初期,大伙烧蜂窝煤,捡的垃圾主要是煤渣。除了煤渣,那就是废纸废书了。那会儿垃圾可‘重’了,到了晚上,腰酸背疼。”
1953年,由于市民开始节柴烧煤,广州的生活垃圾中出现了煤灰,从此拉开了长达40多年的煤灰时代。由于居民烧煤的迅速普及,每天产生的煤灰量很快超过了普通生活垃圾。1996年广州市政府提倡居民使用煤气,机关、单位都不准烧煤后,蜂窝煤的生产和销售走向没落,垃圾中也再难寻煤灰的痕迹。
1972年以前,广州人的生活水平不高,垃圾成分比较简单,多是餐厨垃圾,像烂菜叶、剩饭之类,垃圾直接被运往临近郊区堆肥,参与大自然净化和循环。但随后,一个分水岭出现了。1970年代后,随着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垃圾成分变得复杂了,塑料、塑膜纸、玻璃、电池、有毒金属等构成了垃圾的主体。
而生活垃圾中,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城市居民的日常食品改为冰冻、干缩、预制的成品和半成品,家庭垃圾中的瓜皮、果核等食品废弃物大为减少,而各类纸张或塑料包装物、金属、塑料、玻璃器皿等大大增加。1978年北京市的垃圾成分为:厨房垃圾中的有机物占20%;金属、塑料、废纸占10%;碎砖、瓦砾、渣土、煤灰等无机物约70%。而根据最近抽样调查显示,城市生活垃圾中有机垃圾(厨余、果皮) 占44%,废纸张、废塑料和废金属约占37%。特别要指出是,在生活垃圾中,体积的80%、重量的17%是包装物。
此外,垃圾组成另一个变化是:废旧的家庭工业消费品大幅度增加,如废旧的汽车、摩托车、电视机、电冰箱、旧家具等数量迅速增长。
对捡了20年垃圾的庄清臣来说,捡垃圾也有规律可循,并不只是靠运气。
经济不景气时,固体垃圾比经济景气时期略减,特别是建筑垃圾会大幅度减少。夏季是垃圾里含宝贵的啤酒罐和汽水罐最丰富的季节,也是垃圾中纸类和塑料比例最低的季节。
垃圾的性质也会随不同人类居住而异:含有大量“名牌”食品饮料外包装的垃圾,一般来自中等收入地区,而富裕社区最可能丢弃的是不含酒精的低热量饮料和有品牌的一般食物包装;相比外地,老广喜欢煲汤,垃圾中的水分含量比较大,捡垃圾的时候要注意戴上手套,别得了皮肤病。
相比叔叔那一代拾荒者,老马觉得自己运气不错。不过有时候他也发愁,现在电器都是用塑料做壳,不像以前都是铝铁等金属,不值钱了!现在大家都上网了,买报纸和书的人少了,那可是拾荒收入的主要来源,虽然现在只卖4毛钱/斤,与2008年上半年的每斤八九毛钱相比差了不止一倍。
老马很认真地问记者,金融风暴啥时候结束?这大概是广州超过10万名拾荒者心中共同的迫切疑问。
拾荒者的式微
下午4:20,满载着16吨垃圾的运输车驶进兴丰垃圾场,场内垃圾如山丘般堆积在一起。入口处都是已经使用过的填埋区,上面用帆布覆盖着。垃圾卸车后,工作人员用推土机将垃圾推平,然后再来回压平垃圾。“有用的东西都被拾荒者捡得差不多了,压一压,盖上消毒粉就行了。”工作人员说。在即将被填埋的垃圾中,除了占大多数的塑料袋等生活垃圾外,依然可以看到铝盒、衣物等“好货色”。
广州市环卫局环卫处处长鲍伦军称,2008年广州市生活垃圾达到日产9776吨,除1000 吨被送往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外,其中9成靠兴丰填埋场填埋,从2004年起垃圾日产量每年约递增5%,增幅过快导致兴丰填埋场使用寿命提早8年结束,预计最多只能延续到2012年。这些垃圾中,最多的是厨余垃圾,超过四成,约为3150吨;其次是可回收的纸类、塑料、玻璃和金属,数量大概占四分之一,为 1875吨。剩下的就是竹木、布类等可燃物质和渣石泥土等无机物,前者占14%,后者为19%。
在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周少奇教授看来,真正需要填埋的只有占19%的渣石泥土等无机物,其他均有回收和再利用的价值。像竹木、布类可焚烧发电,厨余垃圾可经生物转换生产沼气,或经适度干燥处理后焚烧发电等。“垃圾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周少奇说。
垃圾资源化,从源头上来说必须先实现垃圾分类回收。但从2007年开始,广州街头的黄绿色分类垃圾桶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蓝色单个垃圾桶。今年4月,广州市环卫局表示,鉴于分类垃圾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新的规划方案出台前,比单桶垃圾箱贵 50%的分类垃圾箱暂时不再投放。2000年,广州被列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但八年多来,这项工作仍然停留在试验阶段。
“中国的具体国情是要靠收购站进行垃圾分类,不能一刀切取消,政府也没有能力收编庞大的拾荒大军。”广州市环卫局局长吕志毅本月在一次“智囊会议”上这样说。在政府眼中,拾荒军团是垃圾分类的重要环节,没有他们,垃圾回收的效率将会更低。
由此,拾荒者们被赋予了自己也不知道的历史使命,走进了城市垃圾回收的环保产业链。但周少奇认为,这种民间分类效率低下,不是科学的垃圾分类处理方式。“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的拾荒不能叫分类,而只是捡走了可以卖钱的东西。一些有害的甚至危险的垃圾根本不能被清除。”
老马倒不奢望带上什么“环保”光环,他只希望自己的“存在”能被确认。“管垃圾场那些人虽然平时对我们睁只眼闭只眼,但有领导来检查的时候,就不让我们开工。”老马说,兴丰管理方不愿承认拾荒者的存在,因为拾荒者与这座垃圾场的国际定位极不协调。
根据《广州市中心城区2010年前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划修编建设计划》,至2009年,焚烧方式比例将超过填埋方式,将会形成以焚烧为主、卫生填埋为最终处置方式。随着垃圾投身烈火化为灰烬,拾荒者的生活和工作空间也将日渐萎缩。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添加“谷腾环保网”